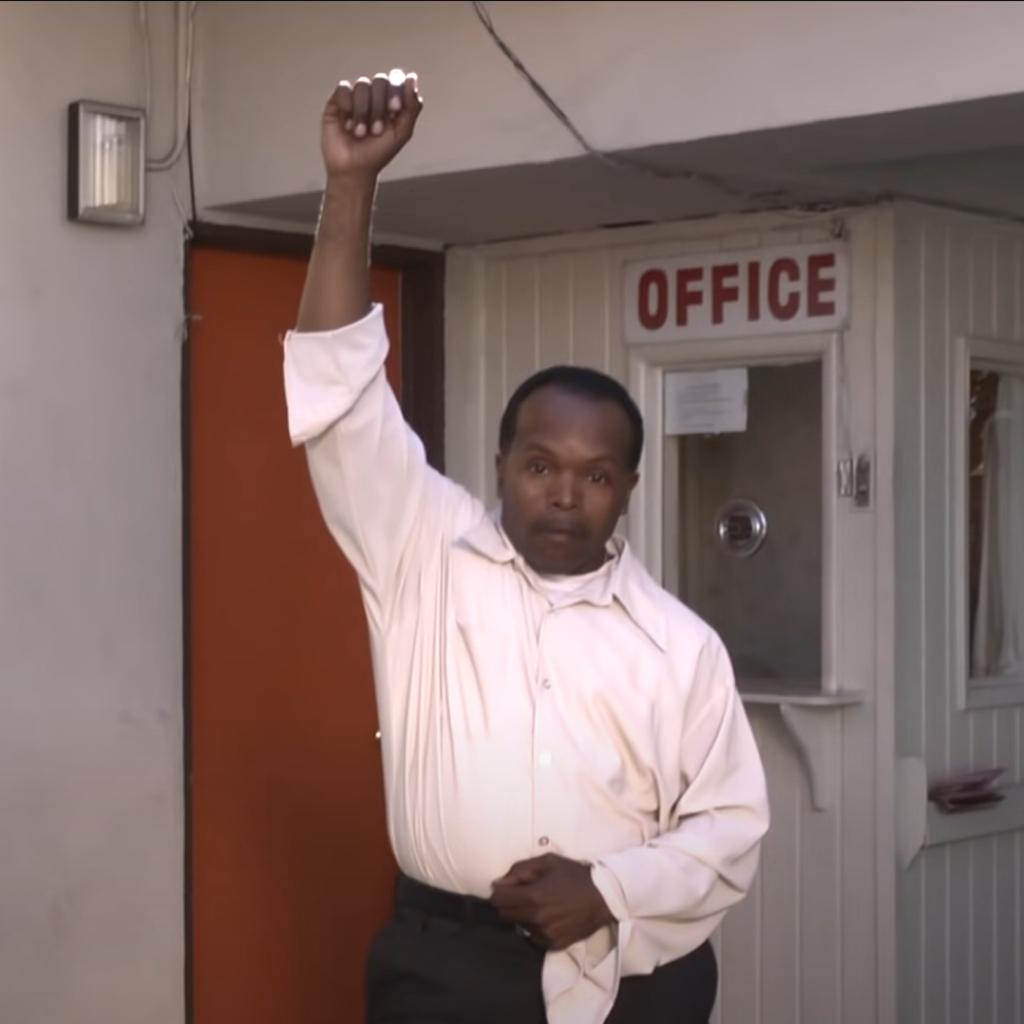Blue Suede Shoes的口头程式:从「One for the Money」说起
过去一年接触到的口头传统这一学科,解决了我不少关于民间音乐长久以来的困惑。为什么民谣歌手可以随意翻唱久远的歌谣?为什么布鲁斯歌手能直接挪用前人的歌曲结构?在过去,我会从版权角度用公有领域来解释。引入口头传统中的口头文学概念后,这些缺乏原创的行为其实是源远流长的知识共享模式,强调原作者权益的“原创”概念在此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口头传统学科的起源,来自对《荷马史诗》如何创作及其作者荷马是否真实存在的研究。学科奠基人帕里和洛德因此创立了“口头程式理论”。简而言之,游吟诗人不需记诵史诗的逐字逐句,而是将故事要素,借助着传统结构,在有限度的变化内重新讲述出来。最终经过漫长的历史和一代代人的吟唱,完全超出个人记忆极限体量的口头文学文本被传承至今。
这里就出现了若干衍生问题,比如,如何界定是否属于“程式”?如何证明传统是口头的?由于史诗流传到我们面前,已经缺乏观众在场,这就又牵扯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以及听众与艺人在表演过程中的互动作用。
将口头程式理论运用在音乐领域是可行的吗?一方面,游吟诗人与民间歌手存在一定交集;另一方面,口头文学也确实包含民间史诗、民俗、谚语、民歌等等。因为没有精力、不是内行,我无法用严谨的学术思维去实证探讨提及的每一个环节,规范每一个用词,只能说将两者进行比较以供开拓思路。
「口头程式」之「程式」
Well, it's one for the money
two for the show
Three to get ready now go, cat, go
这是Carl Perkins 1956年的山地摇滚名曲《Blue Suede Shoes》的开头。在早于Chuck Berry或Bob Dylan的早期摇滚乐中,深刻的歌词含义尚未成为一部作品跻身经典之列的要素。“One for the money”对Blue Suede Shoes而言,没有具体含义,更类似于乐队演奏开始之前确定歌曲速度的“1——2——3——4”,或中国传统曲艺中的定场诗。当Carl Perkins和Elvis Presley演唱或创作这类歌词时,看重的是它们是否朗朗上口,这便是一种对口头而非书面的关注。
“One for the money”的起源,最早能追溯到19世纪。它是赛马或儿童间比拼中的发号施令用语——尽管儿童游戏似乎较少涉及到money与show两个要素:
Vanderlyn, or the Fortunes of an Adventurer (1837)
Charles Hoffman | 作者
Striking for the Right (1872)
Julia Arabella Eastman | 作者
牛津童谣词典所收录的版本及变体为:
口头程式理论的奠基者米尔曼·帕里定义程式是“一种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述某一特定意义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语。”
具体到“One for the money”,money、show便是这一程式中易变的部分,实际使用哪个词,取决于韵律需要——这里将格律降级为韵律,因为对象并非诗歌;而One for the,Two for the则可以认为是保守的传统结构。《诗经》中类似的程式可以更清晰地说明这个概念:
“之子于”后接的六种选择,来自《诗经》的《鸿雁》《桃夭》《采绿》三篇,也就是说,那一时期众多诗人的创作或表演遵循这一程式进行。回到“One for the money”,这一表达便是当时儿童或赛马者共同遵循的口令。到了20世纪末,这句歌词开始被嘻哈吸纳,成为嘻哈歌手常用的句式:
One for the money
two for the bitches
Three to get ready
and four to hit the switches
Snoop Dogg
《Ain't No Fun (If the Homies Cant Have None)》
One for da money
Two for da bass
Three to get ya goin'
'Cuz Da Drat's in da place, yeah
Da Brat《Give It 2 You》
One for the money 每天都赚
日进斗金 掌控着最好的货源
Two for the show Here we go
一登台就引爆 洛城 纽约 Mexico
Three for my real homies
Still hustle still f88k tha police
夏之禹/FBR《Converse》
「口头程式」之「口头」
“One for the money”如何经过大半个世纪流传到Carl Perkins,又如何从Blue Suede Shoes进入说唱,在本轮检索中我还未找到可以考证的资料。令人欣慰的是,当传承链来到嘻哈这一环时,又回到了口头的领域。
众所周知,嘻哈源自西非griot的吟游传统,从基因上就属于口头文学,它并不追求创作固定的书面文本——虽然如今的嘻哈,已不再限于freestyle那种对口头技巧和应变能力的追求。在数字音乐时代,预先创作好的歌词被准确无误地打包在滚动lrc文件里,其中大量习语却依旧来自社群的口头语言,随意可变。说唱歌手在现场表演时,更不会照搬原版本的逐字逐句。只不过相对于创作的嘻哈歌曲相对而言,freestyle更能触摸到嘻哈的本源精神,更“keep it real”。
口头程式理论奠基人艾伯特·洛德提出习语构成程式的三要素是格律(meter)、有用(usefulness)、重复(repetition)。洛杉矶说唱歌手T-Love则提出,说唱作为一种自由表达的音乐,仅有的限制是押韵、可被理解、合拍(如果有伴奏)。再进一步,在freestyle battle中,观众对于说唱歌手的评判大多也基于flow、punchine、clarity(不尬押)等类似的维度。从这个角度看,说唱与广义上的口头程式较为相似,使用一定的公式帮助即兴创作,用词大多来自社群公共的口头语言,但不像史诗使用传统格律和词库,因为它所关注的是个人表达和独创性。
嘻哈、尤其是freestyle的“程式”可能包含两种解释:其一是常用韵脚库,以此衍生出互猜韵脚的嘲讽行为;其二是公式化句子,如“接下来我在这里freestyle,我的freestyle就是最强”一类对主题没有帮助,仅仅满足押韵条件的句子,用来留给自己思考后续句子的时间。以上是针对整首作品而言,像“one for the money”在嘻哈中的使用,就更接近传统的口头程式,作为成为日常用语进入了说唱歌手的语料库。
口耳相传是一段历史过程中一群人的行为,当对象聚焦于一个微观目标*乃至个人**时,口头程式不再涉及大量文本的记忆,也很少肩负客观的传承作用,此时我们应该关注这一理论的“口头”部分,”程式“部分,还是”即兴“部分?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进一步探讨。
*比如前文提及的freestyle battle;
**另一个有趣的命题是分析台湾“急智歌王”张帝如何即兴创作,如他对衣期辙韵脚(i,ü)的严重依赖。
参考资料,除文中已提及的之外:
Hip Hop and Oral History Turning Students into Griots for a New Age (2008), Mark Naison
A Furified Freestyle Homer and Hip Hop (1996), Erik Pihel
史诗的诗学——口头程式理论研究 (1996), 尹虎彬
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 (2000), John Miles Foley
Genuis, Wikipedia相关词条
感谢贾兰贡献文中部分嘻哈曲目
来我厨房
my mind is ramblin‘